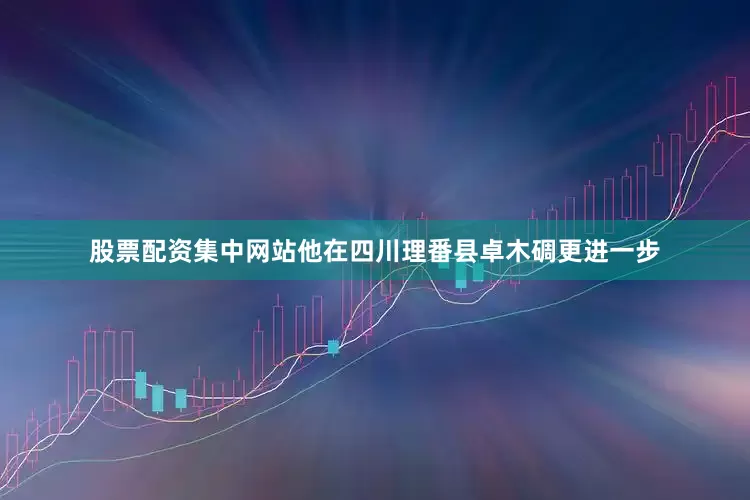
曾是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群体的一员,手握重权,最终却以国民党弃子的身份,在异国他乡凄凉离世。这并非突发事件,更不是简单的选择失误,而是一个人长期以来性格弱点、权力欲望膨胀以及投机本质不断演变的必然结果。
在联合抗日的关键时刻,这样一位资深领导人的出走,无疑给当时党内外带来了巨大震动,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理想信念与个人品性的深层联系。
叛变并非无迹可寻
时间回溯至1927年,彼时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破裂,正当革命面临严峻考验。我党内部积极筹划南昌起义,以建立一支属于人民的独立武装力量。

然而,在这一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关键时刻,一位核心成员却突然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我们应该回到广东,从南方北上进行革命,并搬出“共产国际要我们停止冒险”的理由,试图阻止即将到来的起义。
这个提议与当时急需建立军队的革命现实格格不入。即便他搬出共产国际的名义,也没能动摇同志们的决心。邓中夏坚定地告诉他,无论他是否同意,这场仗都必须打,作战计划已经敲定,贺龙将担任总指挥。
他对此表示不满,质疑贺龙的出身和身份,称其为“土匪”,并以贺龙非党员为由进行阻挠。但周逸群解释说,贺龙是穷苦出身,仗义疏财,且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意加入共产党。
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恽代英更是直接警告,如果再动摇军心,就要将其“打倒”。最终,面对孤立无援的局面,他只能“妥协”,但内心并未真正认同,这埋下了日后冲突的伏笔。
1931年,他结束了在苏联的留学旅程,回国后被任命在鄂豫皖根据地担任要职。在他的领导下,红四方面军实力迅速壮大,部队规模日益扩充,表现一度十分抢眼。
然而,权力的滋长也伴随着个人品性的变异。为巩固自身地位,他在红四方面军内部掀起了一场残酷的“肃反”运动。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指导员,遭受了指头钉竹签子、捆绑吊打等非人酷刑。
数千名同志因此被残忍杀害,这充分暴露出他心胸狭隘、独断专行的一面。这支本应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在他治下却沿用了旧时军阀的陋习,甚至出现了打骂战士的情况。

1935年1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关键会议,恢复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为革命指明了方向。
然而,当时远在川陕根据地的他,却对会议的决定极度不满。他认为此次会议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因此“不合法”,不能随意改变共产国际的既定决策,更反对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集中主力北上。
同年6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党中央考虑到团结大局,将他提升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甚至周恩来同志为了大敌当前能够拧成一股绳,还以自己感冒为由,将红军总政委的职位让给了他。
手握多项权力的他,并没有将重心放在如何带领部队赢得胜利上,反而更加沉迷于手中的权柄。在随后的沙窝会议上,他再次提出了南下主张,列举了北上的诸多“不利因素”,认为即便到达陕北,也不利于军队的驻扎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
当时红军仍在长征途中,背后国民党军队紧追不舍,若选择南下,无异于自投罗网。尽管无人支持南下,他仍与博古等人激烈争辩。
面对争执不休的局面,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同志出来打圆场,提议现场举手表决。结果,只有他一人反对继续北上。这个结果在他的意料之外,却在张闻天的预料之中。
张闻天清楚,他与在座各位同志的立场早已不同,甚至曾向毛泽东同志预言,若继续如此下去,他将来必定会“组织第二党”。这并非张闻天不信任他,而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极端的右倾分裂主义的实践者。

仅仅一个月后,他致电徐向前等人,以“决不会做瓮中之鳖”为由,拒绝继续北上。同年9月10日,他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的刊物上公然发表文章,题为《为争取南下每一战役的全部胜利而斗争!》,声称“我们的红军决定大举南下”,并号召大家“紧急动员起来”。
此外,他还挂起了“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的横幅,进一步煽动分裂情绪。为了争取更多人的响应,他于一周后召开会议,当众宣读了所谓的《阿坝会议决议》。这份决议公然攻击党的领导人,诬蔑党中央的北上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反而美化自己主张的南下路线为“进攻路线”。
决议甚至以“纪律制裁”的方式,打击那些不支持南下主张的同志。10月5日,他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更进一步,公然宣布另立“中央”,自封为“临时中央主席”。
他还擅自“开除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党籍,并下令“通缉”并“捉拿”这些党的领导人。同时,他还下令“免职查办”那些继续支持红军北上的叶剑英等人。
毛泽东同志等人并未将他的“通缉令”放在心上,反而他自己乱了阵脚,试图通过共产国际来压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然而,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早已看清他的真面目,鄙视他破坏革命组织、窃取革命成果的行为。
林育英在给他的回电中明确指出,他所成立的“临时中央”不过是“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并高度赞扬了毛泽东等人带领红军北上的正确性。在共产国际那里碰壁后,他又遭到中央政治局的反对,他成立的“第二党”在国内外均不被认可。
最终,他不得不选择宣布取消这个刚成立没多久的“临时中央”。红军到达延安后,中央开始大力整顿。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1937年3月,党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处理他的问题。

会上,张闻天同志代表政治局宣读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该决定明确指出,他的行为并非突发,而是一朝一夕养成的,并强调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与当时的组织管理不善有关。
决定多次强调“不要变为党的叛徒”,旨在提醒所有同志时刻保持良好的党性。这是我党首次对他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如此严肃的处理。他见形势对自己不利,为了保住党内的地位,会议结束后不久,便向组织提交了《我的错误》。
他在报告中表示自己已经认识到以前所犯的错误。组织考虑到他是一名老党员,便没有继续深究下去,给予了他改过的机会。然而,他并没有深刻反省,反而心生怨恨,认为所有同志都在排挤他,认为党组织已经容不下他,这再次点燃了他内心“叛变”的火苗。
祭祖途中的异心
时间来到1937年7月7日,日寇在卢沟桥悍然制造事变,这标志着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毅然放下与国民党之间的恩怨,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递交给了蒋介石,明确表达了联合抗日的主张。
日寇的入侵激发了社会各界日益强烈的抗日呼声,加之1936年底“西安事变”的推动,蒋介石不得不最终同意国共两党合作,共同驱逐侵略者。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方面公布了国共合作宣言,标志着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开启。
此后,每年清明节,为了向全国人民展示国共两党“团结一致”的姿态,国民党都会邀请我党共同前往黄帝陵,祭拜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国民党与我党之间的和平相处,有利于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怀,鼓励更多人投身到保家卫国的事业中去。

因此,我党并未拒绝国民党的这一提议。1938年4月初,党中央开始商议派遣哪位同志作为代表与国民党代表一同“祭祖”。毛泽东同志心中本已有人选,然而,他却突然“主动请缨”,坚称自己愿意前往黄帝陵。
显然,他此时已在为自己的叛逃行动做着准备。毛泽东同志虽然洞悉他内心的“小九九”,一开始并未同意。但经不住他软磨硬泡的坚持,最终只好派他前去。
目的达成后,他显得异常高兴。1938年4月2日,他带着秘书和一班警卫员,乘坐汽车从延安出发,驶向黄帝陵。抵达目的地后,他与国民党的代表蒋鼎文一同参加了祭祀活动,随后两人进行了秘密会谈。
按照原定计划,他一行人本应在第二天返回延安。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命令警卫员先行返回,谎称自己要去西安寻找林伯渠商量要事。支走了警卫员后,他与秘书张海在蒋鼎文的安排下,住进了国民党的招待所。
在此期间,他秘密会见了多位国民党要员。国民党方面对他许以高官厚禄,他信以为真,这使得他投奔对方的决心更加坚定。会见林伯渠之后,他便在两名特务的护送下,前往武汉。值得庆幸的是,他的秘书张海意志坚定,没有选择与他一同背叛组织。
周总理苦口婆心
1938年4月7日,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工作的林伯渠,突然接到一通电话,要求他前往火车站一趟。打电话的人,正是张国焘的秘书张海。

林伯渠带着疑惑赶到火车站,见到了已身处火车上的张国焘。这趟火车的终点是武汉,林伯渠当即生出不好的预感。武汉可是国民党的地盘,张国焘前往那里的意图,几乎不言而喻。
果不其然,张国焘一见到林伯渠,便开始声泪俱下地“诉苦”,称自己在延安“处境艰难”,并“遭受了不该有的批判和待遇”。他表示不想继续留在延安,要去武汉投靠国民党。
得知张国焘竟然要投靠国民党,林伯渠感到难以置信。但他更清楚,张国焘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一旦“变节”,将可能动摇极少数人的心,对党的发展极为不利,毕竟他手里掌握着不少关于我党的核心信息。
于是,林伯渠苦口婆心地劝说张国焘回心转意,不要背叛自己的信仰,回延安才是正确的“岸”。但张国焘心意已决,如同吃了秤砣一般,铁了心要去武汉。火车即将启动,林伯渠只能选择下车,回到办事处后,他立刻将张国焘的情况紧急上报给了中央。
1938年4月8日一大早,周恩来同志正在办公室处理公务。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只见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兼机要科科长的董小鹏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将两封重要的电报递交给他。
周恩来一边看着电报,一边脸色愈发凝重,神情显得十分严肃。两封电报中,一封来自于林伯渠,他在电报中明确指出张国焘表示“延安待不下去了”,不顾自己的劝阻执意要去武汉投靠国民党。
另一封电报则是中共中央发给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正在武汉的他,务必想办法找到张国焘,劝说其及时醒悟,早日回到组织工作。鉴于张国焘作为共产党核心领导层的成员,他的叛逃将对我党带来巨大影响。

为了尽力挽回他,周恩来同志立即召集李克农、邱南章等人前来商议对策。周恩来向他们详细讲述了张国焘可能叛逃的基本情况,并吩咐他们最好能在火车站截住张国焘,将其带回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尽力劝说他不要执迷不悟。
李克农认可周恩来同志的策略,随即带领童小鹏、邱南章和吴志坚等同志,秘密潜入火车站进行搜寻。直到1938年4月11日晚上七点,他们才在最后一节车厢内搜查到了张国焘的踪迹。
虽然李克农同志个人非常厌恶张国焘此前的作为,但他依然礼貌地与张国焘打招呼,并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周副主席派来接您的。”张国焘闻言,顿时慌了手脚。
他来武汉是为了会见蒋介石,没想到还没见到人,就先被找到了。他身后的两名国民党特务也显得非常惊慌,因为他们没想到一到武汉就遇上了共产党的“特工之王”李克农,因此不敢强行带着张国焘逃离。
见张国焘不愿下车,李克农示意同行人员将他“架”起来,一左一右,半强制性地将其拽下了火车。当晚,周恩来同志带着叶剑英、博古等人,来到江汉路的一家旅馆,与张国焘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
周恩来等人希望与张国焘好好聊聊他从西安私自出走到武汉的事情,然而张国焘却始终避重就轻,只顾大谈宏观政策方针,根本不提自己为何会出现在武汉。博古同志再也忍不住,直接批评了他的叛逃行为。
在场的其他同志也纷纷表示,“你不应该不报告给中央,就私自出走。”张国焘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了组织纪律,但他却将私自出走的原因归咎于“中央对我的批评和处理太过分了”。

周恩来等人闻言,才意识到张国焘一直都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反而始终怨恨党组织对他施加了所谓“不公正”的待遇。他甚至抱怨道:“只让我当个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太不公道了。”
这充分暴露出他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依然追求权力至上的心态。周恩来同志当即严肃指出他的错误:“你几乎毁灭了红军,毁灭了党。”
叶剑英同志建议张国焘回到我党在武汉的办事处居住,毕竟是共事多年的老相识,有问题也好商量。但张国焘执拗地拒绝了。周恩来同志见他依然固执己见,于是让他给中央发一份电报,交代两个内容:
首先,承认自己私自出走是错误的;其次,请求中央安排今后的工作。随后,周恩来同志也向中央发了一份电报,详细汇报了张国焘抵达武汉后的情况。
中央书记处很快给周恩来同志回电,并请他转达给张国焘。电报内容首先表达了对张国焘的关切之情,接着强调目前国内正处于战乱时刻,党内更应保持团结一致,最后期待他能早日回到组织工作。
周恩来同志见张国焘看完电报后没有任何反应,于是再次提议让他回到办事处居住,并借此机会好好聊聊。然而,张国焘坚持住在旅馆,不肯回去,他还向周恩来同志“诉苦”,请求“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声称往后不想再过问政治,只想当个普通老百姓。
次日晚上,即1938年4月14日晚上,周恩来同志再次带着李克农、博古等人前来劝说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去。见周恩来同志一直劝说无果,李克农同志便果断地将张国焘推上车,送到了办事处。

同时,他安排邱南章等同志寸步不离地看守着张国焘,以防他再次逃脱。然而,即便张国焘到了办事处,他也不肯与大家聊任何实质性问题,而是整天想着出去溜达,先后会见了国民党的陈立夫、陈独秀等人。
后来,他的行为变得更加过分,甚至直接向周恩来同志提出要会见蒋介石。考虑到如果不让他见,他一定会私下设法会见,那样反而更难掌握情况,因此,周恩来同志决定不如直接把这件事摆在明面上。
于是在1938年4月16日,周恩来同志亲自带着张国焘一同过江到武昌,去会见蒋介石。张国焘一见到蒋介石,便立刻谄媚讨好地说道:“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他这番话的意思是,过去这些年跟随共产党是“糊涂行为”,现在自己“醒悟了”,要转而追随国民党。周恩来同志闻言,十分生气,当场反驳道:“张先生这些年为革命吃苦,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怎么能说糊涂呢?”
接着,张国焘竟然开始向蒋介石汇报陕甘宁边区的一些情况。要知道,陕甘宁边区的事情是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基本上没有必要向蒋介石交代。他的行为完全像一个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而他的上级根本不是蒋介石。
毫无疑问,此举是他向国民党递交的“投名状”。蒋介石并非傻子,碍于周恩来同志在场,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短暂地与张国焘聊了几句,便安排人员送他们离开了。
会见结束后,张国焘认为自己应该再去见见蒋介石,不能就此放弃投靠。周恩来同志需要回办事处处理大量工作,而张国焘却坚持要去配眼镜、看牙医。李克农同志只好给了吴志坚一些钱,让他跟着张国焘。

实际上,这些都是张国焘在寻找理由脱身,吴志坚只能陪着他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乱逛。绕了一大圈后,张国焘仍坚持不回办事处,邱南章同志只好将他安置在中山路太平洋饭店。
执迷不悟终成空
周恩来同志听到邱南章的汇报之后,决定进行最后一次努力。1938年4月17日上午,周恩来同志一行人再次来到太平洋饭店,会见张国焘。
大家与他聊了许多,但发现张国焘还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去意已决。于是,叶剑英等同志向周恩来提议:“已经劝说一个星期了,没有再继续劝说下去的必要了。”
周恩来同志考虑到还有其他重要的工作要做,同意不再强求,而是给张国焘提供了三条出路,供他选择:第一条,服从中央安排,回到办事处,回到党组织工作;第二条,向组织请假,趁着假期好好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反省自身;第三条,公开发表脱党声明,同时我党也会对外公布开除他的党籍。
换句话说,第三条路就是通向国民党的。听完这三条出路,张国焘没有当场给出答复,而是提出“容我考虑两日”。周恩来同志一行人同意了他的请求,带着其他人离开了饭店。
然而,周恩来同志他们前脚刚走出饭店,张国焘后脚就立刻拨通了戴笠的电话,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久之后,两辆黑色的小汽车停在了饭店门口,从车上走下来几名国民党特务,直奔张国焘居住的房间。

接着,便出现了邱南章所见的那一幕:张国焘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随即跟着那些国民党特务迅速离开了。邱南章同志发现这张纸条后,立即将其拿到我党驻武汉办事处,交给了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明白了,中央给予张国焘三条出路,他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事情紧急,周恩来同志立即连夜起草电报内容,向中央汇报张国焘脱离党组织的情况,并建议开除其党籍。
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将这个决定向全党以及全国公布,正式宣布张国焘自此与党再无瓜葛。
离开了共产党,张国焘自以为迎接自己的将是荣华富贵和高官厚禄。为了向蒋介石和国民党表达投靠的诚意,他甚至主动申请去策反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与特务们一同对我党进行对付,然而效果甚微,几乎没什么成效。
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来说,张国焘这颗棋子未能发挥预期的作用,价值已尽,可以抛弃了,先前许诺的高官厚禄也随之作废。他作为一名“外人”,在国民党内部的处境变得异常尴尬。
1949年末国民党溃败后,他先是去了香港,随后又移居到了加拿大。张国焘曾几次写信给毛泽东同志,希望能够回国,甚至重新回到党内工作。宽容大度的毛泽东同志答应了他,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希望他能够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
然而,高傲自负的张国焘怎么可能答应这个条件,因此他回国一事被无限期搁置。在加拿大,他过得非常凄惨,最终与妻子一同住进了养老院,晚年整日挨饿受冻。1979年,张国焘最终在养老院里活活被冻死,结束了他悲凉的一生。

结语
张国焘的悲剧结局并非偶然,他曾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却最终在异国他乡凄凉离世,这无疑是他个人品性、权力欲望与投机主义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他始终不愿反思自身错误,对党组织的宽容与挽救置若罔闻,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通盈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